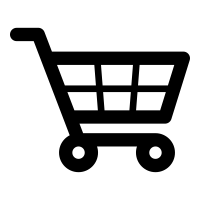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10 (原创天地) 4999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我们二连的驻地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干校把劳改农场接收了下来,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迁移去了青海,上那没有人烟的地方新开荒地去了。1969年底刚到干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住集体宿舍。那个集体宿舍跟监狱一模一样,因为它本来就是关劳改犯的监狱。那是一个每个边长有四五十米的正方形大院子,院子只有一个大铁门可以出入,院墙足有5米高,上面还有电网。院子对角的两个角上建有两个高高的岗楼,每个岗楼可以控制两面墙,所以四面墙下没有任何死角。院子的大铁门一到晚上就锁上,原先劳改犯们在的时候锁上,现在换成计委的干部们了每天晚上仍然锁上,唯一的不同是过去铁门是从外边锁上,怕劳改犯半夜逃跑,而现在是从里边锁上,怕劳改犯半夜进去杀人。因为那时候还有最后一批劳改犯没走,按当时的观念劳改犯就是阶级敌人,而干校又占了他们的农场,所以要防着他们搞阶级报复。院子里面对面有两排长长的平房,作了二连全体五七战士的宿舍,按性别不按年龄,所有的男人包括男孩住西边一排平房,女人包括女孩住东边一排平房。还是睡大通铺,不过已经有床板了。床板全是双人床板,一个挨一个排起来,从房子的这头一直排到另一头。靠两面墙排了两排,中间脚顶脚又排了两排,这大平房里一共排了四排床板,要睡上百人。因为人多床板少,因此我们刚回去时每张双人床板上要睡三个人。我和柳青(柳随年的儿子)、刘建军,我们三个初中年龄的孩子睡一张床板。厕所和盥洗间都建在西南角上。厕所是旱厕,一边是一溜长长的尿池子,另一边是一溜七、八个蹲坑。盥洗间就是两溜水池子和水龙头。院子的北边还有一排平房作了仓库,各家带来的箱子都放在里边。我们带去的两个箱子在那间仓库里放了半年,因为没有自己的地方可以放,都是谁家需要什么了就到那间仓库去找自己家的箱子,开箱子拿东西。仓库也不锁,各家的箱子也都不锁。那时候的人谁也没有对东西的占有欲,因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说不定一道命令就又开拔去哪儿呢。
因为老这么挤着住集体宿舍不是长久之计,而那时谁也不知道这干校要办几个月,几年,还是永久办下去,因此最急迫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那时解决什么问题都是自己动手靠自己,于是各连都开始自己建房子。我们从官渠回到二连后,二连正在大兴土木,每天的劳动都是盖房子。从官渠和韩营回来了几十个孩子,小学的孩子都跟着自己的家长,像我妹妹就归入二连二排的编制。我们这些初中以上年龄的孩子单独编了一个青年班,从那天起我们就不再是孩子而是青年了。干校对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或青年没有半点优待,我们也要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每天早上连长安排当天的活儿时,除了各排的任务之外,从现在开始也再加上一个青年班的任务了。
回到二连的头几个月里,每天的活儿都是盖房子。那几个月里我参加了盖房子的所有工序。除了木匠活儿,因为那是需要技术的。除此之外,盖房子的其它活儿全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儿。我们先盖的几栋房是土坯房,那土坯也是自己制的,除了不用进窑烧以外,制土坯和制砖是完全一样的。制土坯先用粘土加水和泥,和泥时要在土里加上切成小段的麦秆以增加土坯的强度,然后把这泥送进成型机的进料口,从另一侧的出料口出来的就是经挤压成型的砖坯了。不过那个成型机是个很原始老旧的机器,经常出故障,有时候还会伤人,我就亲眼目睹了一起伤人事故。有一天是我们青年班和四排在制土坯。正干着,只听到一声惨叫,一看,原来是轻工局的女干部洪嘉禾不知怎么搞的把右手给卷进成型机的进料口里了。幸亏机器给卡住而停了下来,但她的右手却卷在机器里拿不出来,那进料口上全是血和泥。大家都慌了,有人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因为她已经浑身瘫软了,有人不停地安慰她和她说话,使她不至于昏迷过去,有人赶紧往医务室跑去找医生,剩下的人都围着这台机器商量怎么能把洪嘉禾的手弄出来。有人说让机器倒转使她的手退出来,多数人反对说万一弄错了方向连人都卷进去了。有人说把机器拆了,可当时既没人会拆也没有工具。大家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洪嘉禾的脸色从潮红到苍白再到灰黄,人也越来越不清醒了。后来总算医生及时赶来了,给她上臂用橡胶管扎紧阻止继续失血,又给她胳膊上打了麻醉药,然后在她手臂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硬把她的右手给拽了出来。她右手几个指头都或粉碎或骨折,她后来被送回北京去治伤再没回干校,据说她的右手后来就残了。
后来我们就都盖砖房了,当然砖是从砖厂拉来的,我们再不用去碰那台危险的砖坯成型机了。盖砖房的程序是先在地面上画线挖地基。因为都是盖的平房,所以地基挖两尺深就够了。然后要铺上一层三合土,再用夯砸实。一个夯要四个人抬,因此必须喊打夯号子,四个人的劲使到一起才能把沉重的夯抬起来,也才能坚持长一些时间。号子一般是这样喊的:领号的人喊:同志们加把劲啊,然后四个人一块喊:哎咳呦啊,同时在喊“哎”的时候同时使劲,把夯抬得高高的,然后一起松劲,任那夯靠着重力砸下去。一溜房子十间,地基也很长呢,每次都是几个夯同时干,那号子声此伏彼起,也是非常热闹。打好地基就开始砌墙。砌墙时砂浆要饱满,每一层的砖要砌得整齐,在墙角处还要用一根下悬重物的细绳吊线,以保证这墙是直的。墙砌到一定的高度,就开始上大梁,上桁梁,这是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在桁梁上钉木板,木板上再铺油毡。最后,在油毡上从下向上一层一层铺上红瓦,最后在房脊上再扣上一溜脊瓦,一座平房就盖好了。那时候,没有内装修这一说,连内墙都不粉刷,一座房子,从外面看和从屋里看,那墙都是一样的,都是裸露着砖面。由于就是这些工序,熟练了就越干越快,各排之间还展开劳动竞赛,到最后,一个排三、四十人十几天就能盖起一座有十间房的平房。二连总共盖了有十几栋这样的平房,每栋十间,共有上百间房了。有了房子终于结束了集体住宿,以家庭为单位,每家分配一间房,我母亲和我妹妹也分配到一间房。而我则被当成成年人看待,我们青年班的人都不和家长住在一起,像真正的士兵一样,我们仍然集体住宿。当然这时候条件好一点了,不再是上百人的大宿舍,把原来劳改农场的办公室改成了我们的宿舍,我们青年班十五个男生住一大间,另一大间住着十几个女生,其中就有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她比我高一年级,那时也跟着她父亲在计委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分男女界限,也就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不说话,而且她又比我高一年级,因此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我对她的记忆就是她穿衣服很朴素,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朴素,但她比其他女生还朴素,经常是穿一件灰色的上衣,而且都洗的褪色发白了。那栋房子在我们男女生宿舍之间还有一个小间,住了二连的指导员姜巍和他的妻子柳克美。
这时候虽然住宿已经改成各家各户了(除了我们青年班),但也仅是住宿改变了,其他的仍然没有改变,整个连队仍然是集体化,军事化,每天的活动都是靠听号。二连驻地的树上和电线杆子上都有高音喇叭,不论你在哪里都能听得见号声。早上6点,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起床号把大家叫起来。起床后洗漱,然后就吃早饭。一天三顿饭都是以班为单位去炊事班打回来分。我们青年班男班是一个吃饭单位。每次去打饭时去两个人,是按值日表排的。两个值日生拿着两个脸盆就去炊事班了。二连就那么多吃饭单位,炊事班知道你青年班男班是15个大小伙子。如果吃馒头,一个脸盆给你装上30几个馒头,另一个脸盆装满满一脸盆菜。在干校虽然干的活儿不轻松,但吃饭不限量,随便吃,就这一点还不错。比如最近的活儿重,你就可以多要点馒头。到了冬天活儿不重我们也爱多要些馒头,留着晚上搁火炉子上烤着吃,那你多要几个馒头炊事员也会给你。吃过早饭,再听见集合号响,大家就到麦场上去集合。连长或指导员布置当天全连的劳动任务。比如对我们说:你们青年班今天的任务是修渠,或是打井,或是除草。如果是除草,还要告诉我们是在哪块田里。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按照布置去干活了。如果是除草,我们就每个人扛上锄头,然后排着队向那块地出发了。中午和下午的收工还是听号。二连的地块大部分都围绕着二连,而高音喇叭的声音能传出几里地,因此你就是远在几里地以外的地里干活也能听见号声。听见了号声我们才能收工往回返。中午饭和晚饭还是照此进行,由值日生去炊事班打回来吃。晚饭后一般是学习和运动时间。像我们青年班没什么运动要进行,一般都是念报纸学习。干部们大部分时间也是学习,但随着北京的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有时候某一个阶段也会运动升级,比如在70年前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二连各排(也就是计委的各局)都抓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在运动升级的那些日子里,各排晚上几乎天天都是开批斗会,你从那一排排房子前经过时,就能看见各个房间都灯火通明,里面人头攒动,不时传出“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晚上10点钟,第一遍熄灯号响了,这一遍是准备号,这时候你就该准备洗洗睡了,因为再过15分钟,第二遍熄灯号又响了,这时候所有的房间都必须关灯了。
干校像是一个孤零零的据点,和周围的农村和村民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登上二连那座高高的岗楼,向四下里望去,几里地之内都没有一个村庄,最近的是校部所在的太山庙镇,那也在五、六里地之外了。二连接收了这个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农场的几千亩地。这几千亩地全分布在二连驻地的周围,因此几里地范围之内只有大片的农田而没有村庄。干校里的干部每天都是集体活动,但从来也没有和周围的村庄发生关系的活动,因此干校里的人也从来不去周围的村庄。对周围的农民来说,他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劳改农场已经换了主人,因为现在在干校的地里劳动的人和原先的劳改犯们从服装上看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是或黑或灰的式样单一的衣服,而且也都是几十个人集体干活,间或还能看到穿军装的人在其中(其实是军代表),也很像是军人看守着劳改犯。老乡们原来没事时从不到劳改农场来,因为这里除了危险的劳改犯就是持枪的军人,因此现在没事他们也不会到二连来。偶尔我们会看到有村民来二连了,那一定是有事而来的。有一次我们正在池塘边上打井,正干着呢,来了一个老乡。那老乡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大木桶,走到池塘边就站住了。我们都很好奇,因为轻易见不到老乡到二连驻地来。带班的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停了工,都围了上去。班长问老乡有什么事,老乡说我是来给你们送鱼苗的。我们一看,他那两只大木桶中果然都是一寸长的小鱼苗,头挨着头,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条。因为天气热,水少鱼苗多,有些鱼苗已经死了,漂在水面上。班长说,那赶紧倒池塘里呀,再过一会儿鱼苗都死光了。老乡说,不急,你们还没给钱呢。班长一愣:还要给钱呀,谁跟你要的鱼苗呀?老乡说,年年这个季节我都来送鱼苗,这都是惯例了,用不着谁要,你们给钱就行了。班长说要给钱我可做不了主了,这得找领导了。为了节省时间,班长英明地决定直接找军代表,因为你就是找到连长指导员他说不定还得请示军代表,这来回一耽误那鱼苗就得全死光了。我们兵分几路赶紧去找军代表,一会儿就把军代表找来了。军代表听老乡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既然是惯例,既然你已经挑来了,既然就这么两桶小鱼苗也没多少钱,那我们就收了鱼苗给你钱吧。军代表说:这两桶鱼苗多少钱啊?老乡说:100块钱。吓我们一跳,100块钱在那时是大钱了,买猪肉能买100多斤呢。军代表说,你这鱼苗怎么这么贵呀?老乡说,1分钱1条,不贵呀。军代表说,我不信,就你这两只桶里能装1万条鱼苗?老乡说,不信咱们数啊。军代表说这小鱼苗密密麻麻的还都乱游这怎么数啊?老乡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杯,说,我这一杯是100条鱼苗,我这两桶能装100杯鱼苗。老乡一边说一边用手捞出一把鱼苗,从指缝中漏掉水,把鱼苗倒进小酒杯里,再捞一把鱼苗再倒进小酒杯里,两下子之后小酒杯就满了,光是鱼苗没有水。老乡说,这酒杯里是100条鱼苗,不信咱们就数数。我们都愣了,从没见过这么数鱼的,等这100条数完,那就是100条死鱼了。但当时没人敢质疑他的方法,那时候我们对老乡都是很尊敬的,能单独出来干事的那肯定是贫下中农,而在文革期间那贫下中农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陈永贵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了(可不像现在的农民和农民工成了弱势群体谁都想欺负两下)。军代表发了一会儿愣,最后叹了口气说,算了,咱们也别数了,就算是1万条吧,如果按你这么个数法,最后我们就剩下1万条死鱼了。军代表一指鱼塘,说:赶快把这两桶鱼苗倒进池塘里吧,然后跟我拿钱去。我们比那老乡还急,赶紧把这两桶热得半死不活的鱼苗倒进池塘里,那老乡乐呵呵地跟着军代表找会计拿钱去了。
完整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