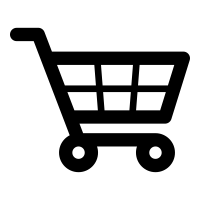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11 (原创天地) 4220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说到军代表,虽说那时各连都任命了由计委的干部担任的连长和指导员,但真正权力最大的还是军代表。军代表的人品和性格完全能决定这些干部的命运,而二连的这个军代表是真把这些干部当成劳改犯了。这些人以前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就是不说他们的职业职务起码也都是细皮嫩肉的知识分子,但在干校他们干的完全是粗重的农活儿。应该说,把他们干的活儿和周围村里的农民相比,他们干的活儿只能比农民干的活儿更重,因为除了正常的农活儿干法之外,还要加上军代表经常性的瞎指挥。计委那时候的总军代表那级别可不低,叫苏静,在1955年第一批授军衔时就已经是中将了。现在的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苏静,因为平津战役的时候他是解放军方面负责和傅作义谈判的代表。但苏静是总军代表,他基本是坐镇在北京,很少到干校来。在干校的每一个连队,都还有一个军代表。驻二连的军代表是一个营级军官,那可是个典型的极左人物,他整天都能独出心裁地想出一些整人的招。因为他不招人喜欢,这么些年了,我早已忘了他的姓名,而且二连就他一个军代表,只要说军代表那就是说的他。
仅举几例他的瞎指挥和整人吧:
有一年又到了种玉米的季节了,一般种玉米就是用拖拉机把土地翻松,然后用播种机播种,或者手工播种也就是抓着一把玉米种子顺着垄沟一溜地撒下去。可是军代表偏不许这么种。他说我们要学大寨(文革语汇,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当时被树立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他们的队长陈永贵,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民,政治地位持续上升,最后竟然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大寨的玉米可不是这么种的。他命令我们每隔两尺的距离挖一个大坑,这个坑必须是圆的,直径一尺,深度一尺。然后在底部铺半尺厚的有机肥,然后不多不少放上三颗玉米种子,最后上面再盖半尺厚的好土。这哪是种玉米,这简直是种树嘛。而干校的地哪一块都有几百亩上千亩,要都这么种玉米,就是把全连的人都累死也种不了多少亩,而且还得误了农时。其实军代表他也是农民出身,他完全清楚玉米不是这么个种法,他就是有意设计这么累人的方法来整治这些不是劳改犯的劳改犯们,还美其名曰说这是大寨式高产试验田的种法。种玉米的季节里,几百上千亩的土地照样是用大型机械耕地播种,而几百个干部就是这样一人一把铁锹地在几十亩试验田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挖大坑种玉米。结果,这块地的玉米基本绝收,因为种子种得太深了,根本就长不出来。但是,结果是没人管的,因为劳动的首要目的是人的改造,而不是收成的多少。
全年的农活中,最累的是收割小麦。因为干校的地多,而且又是机播,光我们二连,每年的小麦都要种几千亩。小麦成熟后,要在十几天中把它全收完,否则麦穗就掉了,或者碰上连阴雨就烂在地里了。干校有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上百亩,本来按时把小麦收完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湖北的天气就是怪,好像特别喜欢和人作对,除了“刮风下雨逢礼拜”以外,越到夏收你怕下雨时它就越爱下雨。一下雨大型收割机就下不了田了,开进去就陷住动不了了。所以每年的麦收,我们都要用镰刀割的传统方式收割小麦。而且,为了抢时间,那十几天是以超出人承受能力的方式干的。麦收有多累呢?每年麦收前,连里都要开誓师大会,而其它的农活是从来用不着开誓师大会的。开誓师大会时,每个排甚至每个班都要上台表决心,甚至有人写血书表决心,好像收麦子是一场让人有去无回的恶仗,每年的誓师大会都透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当然,都是文化人,有时候也会有人以黑色幽默的方式缓解一下悲壮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开麦收誓师大会,基建局的一个年轻干部上台发言,他是这样说的:今年的麦收战役就要开始了,我们班的全体同志个个是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他还有意在说“蠢蠢欲动”时像喊口号一样把声音提高八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第一天开镰开始,疲劳战就开始了。从这天开始,一连十几天,每天早上都改成三点起床,吃过早饭就下地收割。中午在地头吃午饭,由炊事班把饭送到地头,吃完饭继续干。下午吃晚饭还是炊事班把饭送到地头,吃完饭继续干,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收工。走回到宿舍,半夜十一点了,那时人已疲劳到极限,也顾不得脏了,也不洗也不涮了,瘫在床上就睡觉,因为睡不了几个小时,明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号就又响了。一天两天还可以坚持,一连十天这么干,铁人也要累垮了。割麦子最累的是腰,因为割麦子必须弯下腰才行,一天十几个小时弯着腰,所以每个人都喊腰酸腰疼。为了省腰,五七战士们发明了跪式收割法,就是跪在地上割,这样上身基本可以直着,腰就不太酸痛了。那时人们已顾不得姿势雅不雅,顾不得裤子破不破,只想的是怎么能节省一点体力,能熬过麦收那漫长得像是无穷无尽的十天。当然,如果军代表来了,大家就赶紧站起来,让他看见就得训你偷懒,因为跪式收割法确实速度要慢得多。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幅画面,虽已过去近五十年了仍清晰如在昨日:如火的骄阳烤灸下,我的前后左右都是极度疲乏的五七战士,大部分人都跪在地上,低着头一下一下机械地挥动手中的镰刀。所有的人的衣服都是灰色的长衣长裤,虽然天气炎热也不能穿短袖,否则胳膊会被麦穗和麦秆划得全是小口子,汗水一浸疼得钻心。再一个是城里人的胳膊也经不住晒,晒两天就开始一层层地爆皮。所有人的衣服上都蒙着一层白霜,那是汗浸透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之后留下的盐碱。割麦子时我们都不敢抬头看前方,因为前方只见无边的麦浪,似乎永远望不到地头,抬头看只会使人更加绝望。对我们青年班来说,累肯定是累,但更难受的是困,年轻人觉多,谁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三点能爬得起来啊。于是,早上三点起床号响了我们谁都不起来,假装听不见。军代表发现青年班的男生都不在,就跑来砸我们的门,砸得咚咚响,我们只好开门。他质问我们为什么不起床,我们说太困了,没听见起床号。他说,听不见没关系,从今天晚上开始,你们睡觉不许插门,我每天早上来叫你们起床。他还假装开玩笑呢:明天谁不起来我就掀他的被子,用棍子敲他的屁股。我心里说,在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中,为了让长工们早点起来干活儿,地主周扒皮天不亮学鸡叫,起码还找个鸡叫作借口,你则是半夜三点直接进门来敲我们的屁股,真比周扒皮还狠。当然,我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结果,他还真的每天早上来叫我们起床,我们想在床上再磨蹭一会儿也不成了。
这还只是体力上的劳累,有时他的异想天开上来真能整死人。1971年春节前夕,军代表又异想天开了,他说要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春节时改善伙食。那就得听他的,尽管一般是在夏天才捞鱼塘里的鱼。我们把一张三四十米长一人多高的拉网从鱼塘的一侧放下去,然后鱼塘两边每边十几个人拉着网绳慢慢往前走。结果把网拉到鱼塘另一头了,网里一条鱼也没有。有人就说了,因为这网没有贴住池底,所以鱼都从网底下跑掉了。军代表说,那就再拉一网,这一次,人要下水,每隔两米一个人,用脚踩住网底,这样鱼就跑不了了。他这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吓傻了。这是十冬腊月呀,人下水还不冻死!所有的人都不吭声,空气像是凝固了。军代表又发话了:青年班的小伙子们身体好,全都下水,人再不够干部里身体好的也下水。得,我们青年班的人一个也逃不脱了。但光是青年班确实人不够,还得再有人下水。眼看没有人应声,只听我们的连长杨波大叫一声:我带头下,拿酒去!那时二连还自己酿白酒,有人就跑去提了一大桶白酒来。杨波把上衣全脱了,我一看,他简直就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干瘦老头,这下到水里还不冻坏了。他用一个搪瓷大茶缸舀了满满一茶缸子酒,咕咚咚喝了两大口,然后把缸子递给我们青年班,说,每人都喝两口,可以抵抵寒。这时军代表在人群中发现了基建局的干部张强,他那时已被定为是五一六分子,那基本上就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就点名让他下水。张强拿过缸子,满满舀了一缸子酒,就仰着脖子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喝,如果不是被人把缸子夺下来,他那样子是要把那一缸子足有一斤白酒都喝光。都喝完酒,我们都脱的只剩裤衩,咬着牙下到冰冷的池水里。我的天,那已经不是冷的感觉了,而是多少根尖刺扎遍全身的感觉,是头皮逐渐发麻、心脏逐渐抽紧、呼吸逐渐不畅的感觉。我们都双手紧抓着拖网的上边绳,脚踩着下边绳,由两边岸上的人拉着拖网向前走。张强就在我的左侧,我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头了。他眼睛血红,从喉咙里发出像老牛喘气一样的呼呼声。突然,他就不见了,我左边那个位置上突然就没人了。我就对着岸上喊:张强沉底了!可是我光张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因为我的舌头冻得不会打弯了。这回我才知道,俗话说冻得说不出话来是真的,人的舌头如果冻硬了在嘴里不能活动你是一个字也说不清楚的。我只好挥手比划,水里的其他人也发现张强不见了,游过来几个水性好的就在他刚才失踪的地方摸。好在水不是太深,一会功夫他们就把张强捞了起来。大家也顾不得再捞鱼了,几个人把张强抬上岸,别人也趁机都上了岸。大家把张强放在地上,他仍然神志不清,叫他他也不应,只是喉咙里不断发出混浊的声音,证明他还活着。看到他没死,军代表又发话了:还装死狗,来呀,把他给我扔到猪圈里去,我看他还装死不。于是真上来几个人,拉胳膊拉腿像抬死尸一样把他抬起来。二连的一排猪圈就在离池塘五十米远的地方,他们把他放在其中一间猪圈的冰冷的水泥地上。眼看再捞下去弄不好真要出人命了,军代表这才发话说算了今天不捞了。等我们收拾了网具离开池塘时,所有的人都听到猪圈那里传来张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声。军代表说,谁也不许给他送衣服,他冻得受不了自然就自己爬起来了。当天白天,张强没有自己爬起来,当天晚上他仍然没有爬起来,他就那样光着身子在猪圈的水泥地上躺了一白天又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拉到校部医院去抢救。经过抢救,张强没有死,但是腰彻底坏了,他从此再直不起腰,上身永远向前倾45度,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
完整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