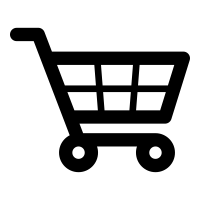童年的九顶山 (原创天地) 4172次阅读
观看【子正】的博客九顶山不是什么名山,而且在北方,地质学上应该算是丘陵。南方与北方多有不同,尤其对于山和水的概念则很是不同。在南方是逢山减一成,遇水加一成,而在北方则刚好相反。南方对于水通常是夸大的,我那时在成都读书,对流经其市内的一条小河便称之为锦江颇觉得好笑,按江河湖泊的顺序,可称之为江的,比如松花江、鸭绿江,应该水面很宽才是。而在北方对于山通常是很夸大的,很小的山,动则称之为摩天岭、凤凰顶,因此,九顶山这名字也很有被夸大的可能。虽然九顶山不高,但对于我来说,比那些我后来到过的名山大川更为印象深刻,毕竟,九顶山是我童年的记忆,九顶山和我童年时发生的一些事密切关联着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强调的童年经历对个体以后的心理发展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对那一段经历至今难以释怀的原因。
如果让我描述,九顶山应该如同庐山的五老峰般的比邻排列开来,只是九顶山是由九座山峰组成的。九个山峰,最高的海拔应该不过千米,环绕成凹字,中间的平坦地带,便是叔父和堂弟一家所在的国营农场。这个农场很大,一大片木栏围成的奶牛场和一大片红砖墙围成的农场鸡舍。这个农场主要供应市内的牛奶、鸡蛋和肉食鸡。我奶奶去世后爷爷续弦,父亲便将叔父带到了C市并供他读书,叔父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国营农场当兽医,几年的功夫便做了那里的场长。
我上小学时, 每年的暑假必定要到叔父的农场和去堂弟玩几个星期。因为差不多每一两天就会有来市内送奶送蛋的车,那时通常父亲会和叔父电话联系好,于是下午三点左右,便会有一辆从市内返回农场的车取道我当时住的部队的院门口来接我。我那时总是性急,总是吃了中饭便跑到院门口等候。有时院门口的卫兵见我背了鼓鼓囊囊的背包坐在门岗亭旁的木头拒马上,便不解地问我一个人要做什么去。即便我告诉了他,通常总还是怀疑为什么没有大人陪着,而且换了岗后不走依旧和我一起坐在门前要看个究竟。当一辆印着C市国营农场的解放牌卡车开到院门口,而我快步跑过去,爬上卡车的装满了牛奶桶的货箱,坐在奶桶上双手抓了高出车厢的护栏并从两个护栏间的缝隙向外望,那卫兵抓着帽子挠头的身影便在一团飞扬起来的尘土中渐渐远去了。
去九顶山,好像每次我都是搭乘农场的吴司机开的那辆送牛奶卡车。那卡车返回农场,驾驶室通常都坐满了人。我从来都不喜欢坐在驾驶室里,我更喜欢坐在后车厢,一边吹着风,一边环看四围的景致。从我家到九顶山大概要开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坐在车厢上总是看着路标计算着何时到达。那时印象很深的便是一路上要经过三个台,一台子,二台子和三台子。之后还要再经过三个洼,大洼,二洼和三洼就到了。车到农场的大门口,通常会看到堂弟和另外五六个孩子在那里,我知道堂弟是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堂弟们一群会随了车跑直到车停下。而我那时在高兴地在车上和堂弟挥手的同时,眼睛会在场部的二层小楼的阴凉处寻找她穿着绿裙子的身影,她的名字叫梅,和我同岁,是吴司机的女儿。
在场部和农场的家属宿舍之间,隔着一座小小的山,山下半环着的是连接场部和宿舍的一条土路。因为走路的距离较远,孩子们大都是喜欢翻山而往返两地之间,于是那小山上也就形成了一条曲曲曲折折的小路。那山上有蛇,偶尔会遇上,于是我们在走山路是,常常随手捡起一根较粗的树枝提在手上开路,同时也防备和蛇的遭遇。在我们一边走一边用树枝敲打开路时,时而远处会飞起一只土鸡,那时我便顾不得草丛里的蛇,直奔那土鸡扑了过去,土鸡通常并不飞得很远,也就七八步的距离便落下,待我再往前追,土鸡就又会飞起七八步的距离落下。那时通常我会听见身后的堂弟和他的伙伴们在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可能抓住那土鸡。那时如果梅和我们在一起,梅也会一起笑起来,我转头看时,竟忘了那土鸡和堂弟一群,满眼里都是梅笑的样子,很是好看,心中诧异女孩儿和男孩子的不同。
农场的家属宿舍是一并七、八间,三排的红砖平房,这里住着二十几户的农场职工。这些房子很大的不同于农家住房,并排的房都是连接着在一起的,前后都有很大的院子,彼此只有一堵单行砖墙,而且很矮,左右的邻居站在各自的院子里便可交谈。那院墙虽然矮,可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有不少的营生,养猪、养鸡鸭鹅、也有养兔子的,很是有些农家院落的意思了。记得那时叔父家养了一只黑色的猪,比起部队院里炊事班养的大花来,胖了许多许多。那大花可能是喂得不好,经常拱出圈来在院子里游走,我们院里的几个孩子见了,常常尾随了大花,突然的急速快跑几步,一跃便骑在那大花的背上,顿时惹得大花大声尖叫,胡乱跑起来直到甩掉背上的人,跑在一旁生气地哼哼。而叔父家黑猪却总是肥肥地懒懒地躺在猪圈里的一处较为干净的稻草上,即便我拿了吃的喊着喂它,它也只是睁开眼看了一下就又睡去,我怀疑那猪是刚刚吃了酒糟的缘故。见那猪不理我,我便会拿起一把蒲叶扇子,对着在猪圈旁放着的一个大的酒糟瓮上面飞舞着的数十只苍蝇一通乱扇,耳朵里听的见“叮”“ 叮”的苍蝇撞击扇子的声音,心里面想着安徒生的勇敢的小裁缝一下打死七个的故事。
九顶山里应该比城市凉爽些,可正午的阳光照射依然很晒很热,许多的大人亦或孩子都有午睡的习惯。记忆里那时每逢骄阳似火的正午,堂弟不是在睡午觉就是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我一个人,无聊得总是去惹那只从不肯站起来的大黑猪,或者去矮墙下和堂弟养的一只兔子玩。那兔子叫青紫兰兔,据说的是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在毒日下,我从墙边揪了草顺着铁丝编兔笼的门递进去,那青紫兰跳过来闻闻,又走开。如果我拿了胡萝卜喂它,它便很快“咔” “咔”磕起来,鼻子上下抽动不协调地配合着嘴的咀嚼。我那时通常会看了发呆,直到眼前的一切变得灰黄晦暗起来,感觉到自己是被太阳晒晕了,站起身来,回到房里,一口气喝掉一大杯子冰凉的井水,意识才慢慢的清醒过来。
其实,那时最好玩的时候应该是晚上。通常晚饭后,孩子们便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有人便喊起来,“喝水”“每个人都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于是几个人便来到谁家的院子里,用手压的水龙头抽出地下的井水来,每个人都使劲喝,喝得肚子饱饱的。之后便弄来些报纸,或坐在门口的石阶、或蹲在院子里叠起蟋蟀篓来。天渐渐黑起来,也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有人拿了雪亮亮的手电,来到场部附近一处有许多的乱石和一个废弃的残破锈蚀的拖拉机架子的空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仔细辨认着来自草从中的发出叫声的蟋蟀的方位。 “我不行了,憋不住了”“快快,这里,这里,往这里照”“放水、放水”“罩住,罩住”。梅有时会和我们一起来,但她不会离我们很近,她只是远远的望着她的年龄比我们小些的弟弟和一群在那里忙忙乱乱着的我们。
在九顶山,我更多的时间是和堂弟跑到鸡舍所在的那片较为平缓的山坡上玩儿。鸡舍用红砖墙高高地围住,墙上端是脉冲电网围栏,每座墙垛上都有环状的白色陶瓷绝缘子将粗粗的铁丝网连接起来,那电网通电时会与那白陶环产生共振,嘶嘶作响很是吓人。鸡舍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即便是职工据说每天上班入舍也要洗澡换衣,主要是因防止鸡瘟爆发的缘故,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禽流感吧。只是因为这种壁垒森严,才引得我更大的好奇心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时堂弟便总是不无得意的告诉我说,几年前没有建鸡舍那会儿,这地方才好玩儿,春夏时满山坡到处都是鸟蛋和土鸡蛋,现在这山坡大部分都被围起来了,所以那些。。。每听到这里,我常常会在巨大的失望之中萌生出一处小小的希望,自以为很合理的推断就是,既然曾经有现在就还会有,既然墙内有墙外就一定会有,急急地催促堂弟起身到高墙外附近去寻那些刚刚被堂弟灌入脑海中的满山的鸟蛋和土鸡蛋,当然蛋是从未找到的,不过破了的散碎蛋壳,倒是偶尔还可以在草丛中、灌木下见到些。
虽然找不到那些被堂弟说成的漫山遍野的蛋,那片山坡上依然有许多的东西可以玩。有一种野生石莲隐隐长在草中的乱石旁,而我对石莲的记忆应该很深。印象里六岁时曾随父亲回山东老家,那时跟了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的老家里的叔叔到一处采石场。那采石场的山坡的石缝中便生长了许多的石莲花,叔叔的车装满了石头准备返程,而六岁的我却赖在那里看石莲花死活都不走,老家里的叔叔就骗我说村子里曾有人因为看石莲花看久了最后变成木头人,这“木头人”三个字由他的那种山东口音说出来,让我觉得那个变成木头的人异常可怕,乖乖跟了他下山。当时见了那些九顶山的石莲并对堂弟说出老家里的叔叔讲过的恐怖“木头人”的事,堂弟听得木然,竟丝毫没有共鸣,如同清晨梦中醒来而对别人说起自己刚刚的梦境般,自己虽依然被那梦境深深感染着,而那梦听在别人的耳朵里,竟全无任何感受。还有一种野生植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正式的名称。这东西很怪,只有一根粗茎长出地面,有一小穗玉米大小,上面长满了爪样的突起,这东西可以吃,酸酸涩涩里隐约着一点点甜的味道。堂弟叫它狼爪子,可我对狼爪没有丝毫概念,那爪样的突起和猫爪有几分象,便怀疑是猫爪的误传。
早起爬上那一片山坡,露水会将鞋和裤管打的湿淋淋。到了九、十点钟,太阳蒸起露水,空气里弥漫了潮湿中夹杂的腐植的味道,原本湿冷贴在腿上的裤管在太阳和体温的共同作用下,也变得温温潮潮,感觉上去倒也舒服。那时,我和堂弟便常常会爬上坡顶,俯瞰下,坡下的那三排职工宿舍的全景和宿舍后面的一个简易木工棚便完完全全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了。那木工棚里只有一位师傅,堂弟和他很熟,我们后来游九顶山主峰时用来开路的竹杖刀,就是堂弟求那位师傅帮忙给做的。我那时在坡顶见那山坡下如鲁宾孙漂流时遇到的小人儿般的师傅在棚里棚外的忙碌,他时而敲打一块木头,那声音总是延后他的动作半拍后才在四周的小山中震响,这声音和动作的不一致,给这山下的小人竟也平添了一种诡异和魔力。
如果是在周末里,在坡顶看那职工宿舍的全景更是有趣,如同动态的一段清明上河图,大、小方格状的宿舍的前院后院,时而有人走来走去。那次,我看到梅的弟弟从他家里揉着眼睛出来,走到后院的侧墙旁蹲下,过了一会见他挥着手向屋里大叫,因为远,听不见他喊什么,一会儿梅出来了,也蹲在侧墙旁。梅的弟弟跑回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又跑到前院,推开门,向堂弟家的前院跑去,推开院门,跑到兔笼旁蹲下看着。与此同时,梅走回到自己家的屋里。梅的弟弟站起身又跑进堂弟的家但很快就又跑出来,接着跑回自己的家里去。之后,梅的弟弟和梅又一起从自己房里走出来,到后院的侧墙旁蹲下并一起做着什么。我很诧异梅和她的弟弟这一连串的动作,转头问和那时我同坐在坡顶的堂弟这是怎么回事。堂弟想了一下说,“可能是梅的弟弟养的母兔发情了,前几天梅的弟弟曾问我能否用我的青紫蓝给他的母兔配种”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动物发情,非常有限联想到的便是我养过的两条热带鱼,那是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玩,见到他家养了一大玻璃缸的好看热带鱼。便同他要了两条,一条有着漂亮的长长红尾的雄鱼,另一条是长着稍短但孔雀开屏状蓝尾的雌鱼。那同学告诉我那雌鱼长到一定的时候肚子就会慢慢变大,雄鱼会不停地追雌鱼,雌鱼被追得累了便会将肚子里的小鱼生出来。后来我的那两条鱼的确生了小鱼,可是我并没有见到雄鱼追雌鱼,我那天放学回家只是见到鱼缸里多了几尾小鱼。堂弟提到母兔发情,我便想到了雌鱼生小鱼,懵懵懂懂中觉得应该就是让母兔生小兔那么一回事。一天晚饭后,梅的弟弟和几个孩子抬着一个大铁笼一起来到堂弟家的前院并放在了堂弟的兔笼旁。我看见梅的弟弟带来的母兔也是青紫蓝兔但个头要比堂弟的那只稍小一些,而且那母兔的脖颈上系了一条红艳艳的毛线绳。我问梅的弟弟为什要给兔儿系红线绳,他很不情愿地说那是梅非要系上不可的。堂弟见了梅的弟弟,表现从未有过的矜持,梅的弟弟软磨硬泡,堂弟终于吐口同意用他的青紫蓝公兔做种兔。当堂弟将自己的青紫蓝兔放入那大铁笼时,这新婚的一对倒也情投意合。只是堂弟那公兔不谙此道,三番五次地跃跃欲试却不得要领,最后一次竟从那母兔身上倒仰下来,顿时逗得围观的这一群孩子哈哈大笑。堂弟顿时满脸涨红,恼羞成怒地伸手将他的公兔铁笼里抱出,要放回他的兔笼内,梅的弟弟再三恳求,好话说尽,堂弟待梅的弟弟答应了带上他爷爷的鸟枪一起去游顶山主峰作为条件后,他才再次将自己的青紫蓝兔放入那大铁笼。
游九顶山主峰的头一天傍晚开始下雨,灰暗阴霾的夜空中远处不停地传来沉闷的雷声。那晚晚饭后我和堂弟冒着雨跑到梅的家去拿梅的爷爷的鸟枪。梅的爷爷将那只老旧但擦的铮亮的气步枪交到堂弟的手中,再三叮咛不要伤到人。待我们拿着枪准备离开的时候,梅的爷爷笑着说道:“明天去九顶山你们会采到很多的蘑菇,听外面的闷雷,每一声闷雷就会有一个蘑菇从地里冒出来的”那晚的夜里我睡在床上,听得屋外的沉闷的雷声轰隆隆似乎一夜未停,我那夜里的梦应该是梦到了九顶山漫山遍野的蘑菇。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六七个孩一起去游顶山主峰,一路上,只有树叶上挂着的不时飘落下来的雨滴和湿润润的路提醒着我们昨夜曾经下过雨,天空却完全晴朗得若无其事,没有一丝云彩,好像昨夜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堂弟扛着枪挑着一个篮子兴高采烈地和梅的弟弟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走在前面,渐渐地将不惯走山路的我还有梅甩在了后面。我记得那天梅穿的依旧是一条绿裙子,配了梅白白的腿异常好看,我和梅走在后面,一路说着话并采着蘑菇。我和梅都说了什么已全然忘记了,但我想我应该是问了梅那母兔是否怀了小兔,或许我还同她要了只即将出生的小兔。不过我记得很清的是那天的蘑菇的确很多,很快梅的篮子和我的篮子都装满了,我们将篮子放在小路边的草中,做了记号准备回来的时候取,然后加快脚步去追堂弟他们。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一行终于说着笑着登上了九顶山的主峰。在九顶山的主峰向山另一边望去,虽然没有王家新【在山的那边】一般的失望和沮丧,但九顶山的主峰的另一侧远没有面向农场这一侧丰富多彩。很陡峭的一面坡可以一眼得见山脚,山脚下一台蚂蚁般大小的掘土机将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挖开很小的一片,露出白色的山体,再远处便是一条公路,我认出那是我来时车绕进农场的那条路。
我从农场回到家里,通常很快也就将农场的事情忘了。不过那一年有一些事情还会时时让我想起九顶山来。那年的秋天,吴司机送来了一只小兔交给了门卫。我放学时在门卫那里得到那只小兔时非常高兴,尤其当我看到小兔的脖颈上也系了一条红艳艳的毛线绳,我知道那是梅系上去的。后来发生的接二连三事情都对我尚未成熟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刺激。那年的冬天快要过年时,一天炊事班的几个人将在院子里游走的大花捉住,仰面朝天地捆在一个条凳上,大花的脖子上被捅了一刀,地上的一个大铝盆接着大花滚滚涌出的鲜血。大花从始至终地惨叫着,一直到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杀大花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九顶山那只从不肯站起来的大黑猪,在这年根儿底下不知它的命运如何。后来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大花的肉,大花的肉做熟了很香,不过我一口都没有吃。大花死后的几天,我的那只小兔也死了,那小兔原本我是放在院子里的一间库房里养着的,不知是什么动物或许是黄鼠狼钻进了兔笼,将那还未长得很大的小兔吃的只剩下了一只头和一只脚。那年的冬天,叔父的一家来我家里过年,在闲聊时,叔父说起九顶山农场里的一件怪事,梅的爷爷突然死在了家里,向殡仪馆要车运尸体,不知什么原故,殡仪馆竟然开来了两辆灵车,当时大家都说不吉利,谁料想,没出一个月,梅也生了病住进了医院,医院诊断是急性白血病。梅好像是住进医院两个月也走了,后来听说,吴司机见到人经常自责自己给梅起的名字不好,本来姓吴,吴就是“无”,偏偏又叫梅,梅就是“没”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说没就没了。吴司机的这话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去年回国见到堂弟,堂弟已结婚并早就搬到市内来住了。和堂弟说起九顶山来,堂弟怔了一下说: “你是说九鼎玉矿?哦,对,对,那曾经是座山,我们小时候还到那儿玩儿过,现在那儿叫九鼎玉矿,去年我还在那儿买过一块玉,那绿色很润很纯。”我听了默然,不敢再问下去,担心出现那年和他说起“木头人”时的尴尬,不过脑海里童年的九顶山的画面一幅幅掠过。堂弟的那快儿玉绿得很润很纯,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我相信他说的话,不过我那时顽固想着的依旧是那条绿色的裙子。
完整帖子:
- 童年的九顶山 - 子正, 2014-07-27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先抢个沙发。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眉子, 2014-07-27
- 眉子, 2014-07-27
- 先顶,慢慢欣赏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修理小子, 2014-07-27
- 修理小子, 2014-07-27
- 中!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大财主, 2016-02-10
- 大财主, 2016-02-10
- 中!
- 正哥写的太好了。佩服佩服! - 眉子, 2014-07-27
- 似曾相识的童年:)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4-07-27
- 丽桥游子, 2014-07-27
- 写的真好,生动。。。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小鱼儿, 2014-07-27
- 小鱼儿, 2014-07-27
- 大诗哥情感文笔都非常细腻,平时嬉笑怒骂的,完全遮掩了光芒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裴幸福, 2014-07-28
- 裴幸福, 2014-07-28
- 正哥亦庄亦谐,大俗大雅。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眉子, 2014-07-28
- 眉子, 2014-07-28
- 正哥亦庄亦谐,大俗大雅。
- 正哥也在这啊? 问个好。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一片老姜, 2014-07-28
- 一片老姜, 2014-07-28
- 写的细腻,栩栩如生。 - 北宇, 2014-07-31
- 先抢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