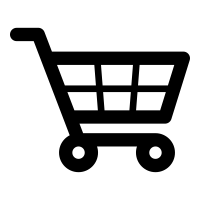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6 (原创天地) 5187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那时候,还兴打群架。有组织的红卫兵是组织对组织地打,那叫武斗。无组织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就以各个大院为组织互相打,叫约架。大院就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在北京盖的家属宿舍,这些宿舍都包括几十栋楼,住上几百上千户人家,而且大院里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场等,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计委大院在这些大院中算是大的,因为它虽然以国家计委为主体,其实还包括了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和国家统计局。计委大院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占了整个一个一区。大院里都是三层和四层的灰砖楼房,一共有300多个门洞,每个门洞有6户,因此有1800多户。每户少算点算4个人(那时还没计划生育呢,所以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整个计委大院里也住了近万人呢。人多,那肯定青年人也就多。计委是国家关键领导部门,高干就多,自然高干子弟也就多。高干子弟多自然就树大招风。计委大院高干子弟多,别的大院高干子弟也不少,尤其是军队的大院。这些高干子弟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想称霸一方,因此就经常互相约架。计委大院那时候约的群架不少,我就亲历了当时最有名的那场公安部大院血洗计委大院的战斗。那是在1967年的夏天,一个消息在计委大院里传开了,说公安部大院和计委大院约架了,而且是没把计委大院放在眼里,他们要“血洗计委大院”。因为公安部大院提前就下了战书了,因此计委大院早早就开始了准备。毕竟公安部大院是要来血洗的,因此计委大院那些日子是有些人心惶惶的。那次战斗的领头人是计委大院的两个高干子弟,曹玉生和曹金生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据说曾当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那时的驻外大使都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像耿飚、黄镇、姬鹏飞那样的老革命,因此曹玉生和曹金生的爸爸是高干是毫无疑问的。曹家兄弟俩也确实是标准的高干子弟打扮,整天穿一身国防绿,挎一个军挎,里面不放别的,就是一把菜刀,随时准备和人打架。在准备的那些天里,曹家兄弟周围时刻有几十个和他们同年龄的男青年,后面还跟着几十上百像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因此计委大院随时都有上百人准备战斗。而且计委大院的准备还颇具计划和规模。首先是把计委大院变成了一座城池,凡是入口都有人把守。因为计委大院的入口很多,因此为了集中兵力,必须减少入口数量,为此计委大院的孩子们居然把好几个十米八米宽的入口都用砖头垒成墙堵死了。我记得清楚的是北建委朝西的两个入口都这样堵死了。几个主要入口每天都有很多车辆出入,是无法堵住的,因此都安排了重兵把守。公安部大院来血洗的情形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来的时间是下午。因为这战书是早下好了的,因此我们都知道当天要有一场恶战。每个入口处都有几十个曹家兄弟那么大的男青年,后面还有几十上百的半大孩子助威。男青年都手持各种武器,我记得曹玉生是手提一根两米长两头粗中间细的大棍。我还记得一个男青年找不到武器,从我们后院的一家阳台上找到一把拖把,用脚踩着把拖把头拽掉,拎着拖把杆当了武器了。我们当时跟着大队集中在中古友谊小学的东南角围墙外面,这位置可真是个战略要地,从这里向东可以增援三里河东口方向,向北可以增援红塔礼堂方向,向西可以增援计委食堂方向。等了没多一会儿,突然从东边就拐过来几十辆自行车,是公安部大院的人冲过来了。这边有人一声令下,几十块砖头就扔过去了,当时就有几个人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随着砖头扔过去,几十人提着重武器向前冲去。公安部的人远道来袭,他们只有皮带钢丝锁等轻武器,而且人也少,因此一下子就被击垮,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战斗,他们是调转车头就跑,跑得慢的就被逮住了。仅仅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计委大院全胜。等我们这第二梯队的半大孩子敢进入战斗核心区了,我看到的是几个头破血流的人自己推着自行车被计委大院的人押着。这是我们这个方向的战斗情况,另外几个方向上的战斗基本相同,都是一阵砖头雨飞过去,都是几分钟解决战斗。计委大院的人很大气,还懂得优待俘虏,把这些人都送到三里河东口的门诊部去包扎伤口了。这场血洗计委大院的战斗我们还没打过瘾就结束了。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么大的群架,从准备到开打前后十几天,几个路口都被砖墙堵了,每天几十上百人在大院里跑来跑去,开打的当天几十个人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可是从头到尾我们的辖区派出所月坛派出所都没有一个警察来过问一下,因为当时整个公检法系统也都在闹革命,基本上都处于业务瘫痪状态,月坛派出所的所长说不定正在所里挨斗呢。
那时,改名字也是一种革命行动,把一个带点封资修味道的名字改成一个红色的名字,那就是有革命觉悟的表现。我并不喜欢我的名字,但我居然没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名字改了,现在想来一是政治上反应迟钝,二还真的就是思想觉悟低,从没想过在改名上革命一把,否则我改个红色的名字说不定就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了呢。我身边就发生了三起改名字的革命行动,至于宋彬彬改名宋要伍的事,那更是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我身边这三起改革命名的例子,第一个又是我母亲。她本来叫苗惠芬,那名字用了几十年,当年参加解放军时都没有改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却改了。我母亲把名字改成苗青了。为什么改成青啊,因为毛泽东的妻子叫江青呗,因此当时很多女性改名为青以示向“江青同志学习”(文革语汇)之意。第二个例子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腾五波的哥哥。他哥哥本名叫腾四初。藤四初是学钢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钢琴已经弹得不错了。那时候有个青年钢琴家叫殷承宗,他因为弹了那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而在全国一炮而红。他并且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夫人江青的赏识,因为江青那时是抓文艺工作的,据说钢琴协奏曲“黄河”也得到过江青的指导,就像那八个样板戏一样。殷承宗为了表示思想进步,把名字改了,因为“承宗”明显具有四旧的性质。他把名字从殷承宗改为殷诚忠了。腾四初跟殷诚忠学过琴,至少是得到过殷诚忠的亲自指导,因此他特别崇拜殷诚忠。于是在殷诚忠成为全国知名的名人不久后,腾四初也把名字改了,从腾四初改成腾诚忠了。你忠于毛主席,我也不落后,你诚忠,我也诚忠,连名字都跟你一样。当然,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江青的倒台,殷诚忠也失势了。于是,审时度势,他把名字又改回殷承宗了。自然,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腾诚忠也不再叫腾诚忠了,他也改回了原名,不过换了一个字,把文化味不太高的腾四初改成了更有文艺范儿的腾似初,后来再改成文化底蕴更浓的腾矢初。如今,腾矢初的头衔已经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国家级著名指挥家了,但当年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俗。第三个例子也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叫马力克。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中国和马列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关系最密切,一个苏联老大哥的称呼,显示出那时中国人对苏联人的亲近。苏联那时对中国的援助也真不少,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在中国进行了156项援助性建设,帮助新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在经济上迅速站稳了脚跟。随着这156项援建项目,大批苏联专家也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中国是“一边倒”(当年语汇)地崇苏亲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马力克的爸爸给他儿子起了马力克这么个苏联味十足的名字。还不仅仅是马力克呢,马力克的哥哥叫马诺夫,他姐姐叫马丽莎,一家仨孩子全是苏联名。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十年代末,中苏就已经交恶了,苏联早从老大哥变成苏修(当年语汇)了。但就是这样,马力克仍然叫马力克。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马力克就不敢再叫马力克了,再叫马力克可能或肯定会连累他的父亲,造反派就根据这一条就可以把马力克的父亲“打翻在地”(文革语汇),说严重点可以说他是苏联特务,差一点也可以说他是苏联的走狗,就这两条都可以使红卫兵们名正言顺地抄他的家,批斗他的父亲,甚至打死他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一家三个孩子全叫苏联名的真不多,这实在是“太反动了”(文革语汇)。所以马力克和他哥哥姐姐一夜之间全改名了,从媚苏崇苏的苏联名一改而成最极端的革命名,马力克改名为马继杰,马诺夫改名为马继峰,马丽莎改名为马继红。今天的人们看不出这几个名字为什么是最极端的革命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看而知:继杰就是继承王杰,继峰就是继承雷锋。王杰是谁?是一个在投弹训练中为了保护民兵而扑倒在爆炸的手榴弹上英勇牺牲了的解放军士兵。雷锋是谁?也是一名解放军士兵,而且是一个据说是只做好事从未做过坏事的士兵。这两个人都是毛主席题过词表扬的人,都是当时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继红呢?红色就是革命的意思,继红就是“继承革命事业”(文革语汇)呗。马继杰和他哥姐在文革后是否改回了原名我就不知道了,我最后离开马继杰是1971年,那时还是文革期间,他仍然叫着马继杰,而且是我们当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人。那时我们都随父母去了国家计委五七干校(文革特有现象),因为我们年龄小,都送到离干校几十里以外的一所农村中学去住校,“和贫下中农子弟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语汇)。那时的生活太艰苦了,仅举两例:一是我是在那个学校才第一次知道虱子是什么样子。我对我的农村同学们说我从未见过虱子长什么样时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我是来自外星。于是有一天我在教室里,几个农村学生兴奋地跑来找我,说我们给你逮了个虱子,装在小瓶子了,你快跟我们回宿舍去看。当然在那天以后,我就经常在自己床上见到这种吸人血的小虫子了;第二是因为天天顿顿吃红薯面,难以下咽不说,还成天胃里泛酸水。有一天食堂准备中午改善一下伙食吃糊辣汤(一种河南饭食,河南人视为美食,糊辣汤之于河南人差不多相当于炒肝包子炸酱面之于北京人),被一个同学无意中发现了,他禁不住在院子里大喊了一声:中午吃糊辣汤喽!结果所有的教室都骚动起来,几百个学生发出的兴奋的低吼声传遍了整个校园,所有的班级都无法上课了。不知哪个班的学生先跑出了教室,别的班的学生一看也往外跑,结果发生了群羊效应,所有的学生都跑出教室往食堂跑,谁都怕去晚了排不上队吃不上这千载难逢的一顿糊辣汤。那天各班老师也都放任了学生们的“无组织无纪律”(文革语汇),那天学校也破天荒地没有处分任何学生和老师。因为农村学校的生活太苦,我们都受不了,就不想再继续在农村学校上学了。有的同学就跑回了干校,说我们不上学了,要和五七战士(文革语汇)们一样参加劳动。我们连那时有个军代表,什么事都得经过他批准。他是个比较左的人,你只要编出个革命的理由他就会批准。“和五七战士一起参加劳动锻炼”这个口号挺革命的,他就批准了,说“愿意继续在农村学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革命,回干校和五七战士一起参加劳动锻炼也是革命”。有他这句话那些跑回干校的同学就再不回学校了。有人带头我们就陆陆续续都回干校了,在干校起码不用天天顿顿吃红薯面啊。我是比较晚离开学校的(我这个人比较迟钝,在哪里一习惯就不想动了),我决定回干校时留在农村学校的干校子弟已经不多了,而马继杰就是其中之一。临走时我去他宿舍看他。他生病了,一个人在地铺上躺着,发着高烧,脸色腊黄,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我说要不你也回干校吧,起码吃的好点,得病了有医务室可以看病。他当时对我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条件艰苦正是对我们的革命意志的考验。我不走,我选择在这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战斗。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而且看得出完全是发自他内心的。我当时觉得马继杰说那些话时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
更可笑的是那时候不但人改名,破四旧最厉害的1966年下半年,连东西都得改名。那时候凡沾洋的都得改名,你再说“洋火”就有人打你,你再说“洋钉”就有人打你。很多蔬菜是多少年前从外国引进来的,名字中就带“西”带“洋”等,这时候全得改名。三里河菜店的墙上有一块大牌子,那上面写着当天的各种蔬菜的价格,有一天我发现好几种菜名都变了:西红柿变成了“鲜红柿”,因为不能有“西”,洋白菜变成了“元白菜”,因为不能有“洋”,黄瓜变成了“青瓜”,因为不能有“黄”。你买菜得对售货员说:给我来两斤鲜红柿。最不习惯的是黄瓜,你说:给我来两斤青瓜,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别扭。当然这种太极端的做法不能长久,所以过了几个月后,当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过去了之后,这些菜名又悄悄地改回了原名。
文化大革命使多少人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上面提到的国家计委的普通女干部李梅、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莫平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他们的生命就这么以一种惨烈的形式终结了。我的命运还没有那么悲惨,但我的生活轨迹也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从天之骄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一帆风顺,命运好过绝大多数我的同龄人。我的父母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的时候进入国家计委工作的。中国那个时候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这个计划就来自于国家计委。所以可以不夸张地说,全中国的所有经济活动,从一年短期的到五年长期的,都是在北京三里河的那座国家计委的九层大办公楼里制定出来的。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国家计委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国家机关。因此,国家计委也是待遇最好的国家机关。作为国家计委干部的孩子,我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计委大院在西城区三里河,而计委保育院却远在十几里外的北太平庄。那是一片像城堡一样的建筑群,被计委接收来作了保育院。远,对别人是事儿,对计委不算事。每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在计委食堂前上车,一溜七、八辆捷克产斯柯达大轿车把几百个孩子送去保育院。每星期六下午,又是这七、八辆斯柯达大轿车再把几百个孩子送回三里河。那时北京的街上汽车很少,进口的大轿车更少,我们这个斯柯达大轿车队就像今天的国宾车队一样壮观威风。保育院院长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据说从延安时期她就在延安保育院给中央首长们带孩子。可以想象,有这样资格的院长,计委保育院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当时最好的。我从两岁到六岁一直在计委保育院度过,虽然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全中国饿死多少人,有说几百万的,有说上千万的,但我们从来没有一点感觉。1962年,到了七岁,我就自然地进了就在计委大院院子中心的三里河第二小学。那时中国和古巴的关系又好上了,北京市要命名一所各方面条件好的小学为中古友谊小学,好随时接待古巴朋友的参观。结果是三里河第二小学被命名为中古友谊小学,这就证明了该小学的设施和师资条件都优于北京市的绝大多数小学。我那时还算聪明,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所以深得我的班主任胡奚辉老师的喜爱。我记得有一次胡老师是这样评价我的: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是爱骄傲。那时如果学校给班里分来什么有名额限制的好活动,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两个名额那肯定有我,如果只有一个名额那八成也会给我。我能记得的是,有一年五一节,我们学校派代表去北海少年宫参加市里的庆祝活动,我们班只有一个名额,就是我去的。上到小学二年级,到了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了,我是第一批入队的,并且立刻就被老师选为小队长和中队委。我从小喜欢画画,那时还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我画的一幅学习解放军的画还被学校作为礼物送给来学校参观的古巴客人。196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这时学校要从各班选出最好的学生参加三轮考试去上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录取的比例是从全北京市几百所小学的几万名二年级学生中只招收四个班180人,那绝对是百里挑一的比例了。胡老师直接就找了我母亲,让她给我报了名。结果我也没让她失望,顺利地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三关,成了那年中古友谊小学唯一考进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我继续顺利,继续是班上的好学生。那时我是中队体育委员,我们班上体育课喊操喊口令就是我。我画画的特长那时在班上也很突出,班里的板报从来都是由我操办。上美术课时,美术老师都是让我先在黑板上画出来,然后下面同学就照着我的画。在法语小班我也是好学生,孟老师那么厉害,但我不记得他曾对我发过脾气。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用多种外语播送中国小朋友致外国小朋友的节日贺信,这个播送就是由北京外国语学校小学部的学生们来录音的,其中的法语贺信就是我和我们法语小班的女同学李爱敏录音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的职业道路可以说是已经确定了的。我将按部就班连校门都不出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的10年一贯制学校),然后上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业,因为到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学了10年的法语了。大学毕业我将被分配到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
可是文化大革命使我这本已是板上钉钉的锦绣前程化为了泡影,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更准确点说是从1967年10月复课闹革命开始,我就再没有轻松舒心的好日子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就开始实行出身论(文革语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没人问你的出身是什么,可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人不但有一个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出身了,而且这个出身完全能决定你的命运。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出身是什么,简单说出身就是往上查三代,看你爷爷在土改时被定成了什么成分(文革语汇,而且本段下面几行将出现大量的文革语汇,我用黑体标出。这些词语现在的人已经看不懂了,而当年那都是使用率最高的词汇)。成分,这又是一个现在的人没听说过的历史名词,文革语汇。根据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所有的中国人或被划归为剥削阶级,或被划归为被剥削阶级,无人能有例外。在农村,地主、富农是剥削阶级,贫农、下中农和雇农是被剥削阶级。还有一个中农,也算是被剥削阶级阵营的,但不算基本力量,算是团结的对象。在城市中,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工人是被剥削阶级。因为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被剥削阶级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被剥削阶级是胜利者,剥削阶级是失败者。在中国,从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候,所有的好事都必须是成分好的人才能有份,而成分不好的人可不仅仅是好事没份,而是想正常生活都不可能。人们如果知道你是剥削阶级出身,可以拿你不当人,可以骂你,可以打你,你若敢还嘴还手,那就叫反动气焰嚣张,那是可以把你打死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我们外语学校的普通女工刘桂兰仅仅因为她是地主出身就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批斗会上红卫兵对她又打又骂,她忍不住还了两句嘴,竟惹怒了这些当年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娃娃,棍棒齐上,竟然当场将刘桂打死在批斗会现场。不幸的是,我就偏偏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因为我的奶奶在土改中成分被定为富农(我爷爷早在土改前多少年就死了所以没有赶上土改,那他的富农成分就落到了我奶奶的头上),因此我们家的成分就成了富农。尽管我奶奶的三个孩子中就有两个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我姑姑和我父亲),尽管我姑姑还嫁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姑父韩正夫是红军时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共产党体制中,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到了解放后基本上都是高干),都仍然无法(或者根本不敢)阻止在土改运动中把我家定为富农。我母亲家的成分是相当好的下中农,但是没用,填成分必须是填父亲家这一边的。所以,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开始,我以前的优越感就荡然无存了,我就再没有过舒心轻松的日子了。所有的好事你都不敢靠前,因为那时干什么都要填表,尤其是好事那更是要通过填表来把地富资本家子弟剔出去的,而那时只要是个表就有家庭出身这(该死的)一栏,而一填家庭出身你就露馅。把你的申请表扔到一边还算是好的,人家完全可以用蔑视的口气奚落你一句:就你这富农的狗崽子还痴心妄想呢。由于出身不好,入红卫兵没我的份,入团没我的份,当兵就更没我的份。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处处向前向上,有好事我可以放心大胆主动争取。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能处处向后,因为只有不去碰那些好事才不会引起查看家庭出身这件事,谁明知不行还自找其辱啊。我那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填表,因为不管填什么表都有家庭出身这一栏,而那时偏偏就干什么事都要填表,甚至不干什么事也要过一段时间就填一次表。每次填表对我而言就像被抓进公安局受审一样害怕和难受,因为平时已被人不注意的富农家庭出身这时就会凸现出来。被剥削阶级当然是大多数,剥削阶级是少数,我们就会显得特别显眼,就好像别人都穿着衣服而我们光着身子一样。那时我不再觉得外语学校可爱了,我只想逃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时军队干部子弟时兴走后门当兵,就是在正规征兵时通过在军队中的老战友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那时当兵不但是避免上山下乡的好出路,而且能走后门当兵也是在军队中有关系的体现,是叫人高看一眼的荣耀。本来我也可以走后门当兵的,我姑父就是老红军,虽然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但在部队中老战友关系还多得是,因此很轻易就把他的两个儿子都送进部队了。那时我父母也和我姑姑姑父商量了,看能否把我送到四川我姑姑家住一段,然后让我姑父找个关系把我送进部队。我姑父说,什么都好办,你近视眼(我是右眼弱视),没关系,你身体弱,没关系,我让他们收他们就得收。就是家庭出身这一关过不去,这是原则,硬杠杠,再硬的关系也没有人敢收的。于是当兵这条路就算彻底对我关闭了。
当兵也当不成,那就只能在学校继续熬着吧。1967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发通知了,上次是停课闹革命,现在要复课闹革命。去年是停课,今年是复课,但不论停课还是复课,都要闹革命。所以虽然复课了,但是也没有好好上过课。首先是真正学习文化的时间少了,被下面所说的“不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占用了,其次是所学的知识中政治性的东西挤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部分,而这些政治性的东西一旦政治风头一过,马上变得无任何用处,对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没有任何帮助。那时的课本中古文是肯定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没有了,因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被打断了。我们的语文课文中,增加了毛主席的著作,但是古诗词没有了,中国古代文学也没有了。那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四大名著都是禁书,像“金瓶梅”那种带有性描写情节的书那更是禁书中的禁书。唐诗宋词中除了少数描写了劳动人民的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纯粹描写风景的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可以列入课本外,其余的统统不见。当代文学我们只知道一个鲁迅,那是因为毛泽东只对他一人评价甚高。剩下的就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这种政治小说了。虽然我们是外语学校,但外国文学却是空白,西方所有著名作家的书都是禁书。像描写了一些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家我们多少还知道名字,如法国作家中的雨果、莫泊桑,左拉等,我们间或可以读到他们的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但他们的完整著作仍然是看不到的,因为书店里除了毛泽东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和鲁迅的著作外,没有其他人的著作。至于像斯汤达和大仲马小仲马等,我们被告知他们都是一些坏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充斥着的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即剥削阶级的贵族小姐是会和被剥削阶级的穷小子谈恋爱的,因此对革命的接班人是有毒害作用的,因此他们的书像“红与黑”、“茶花女”等那更是毒草中的毒草。即使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中我们也只知道一个高尔基,因为他是苏联的革命作家。但是高尔基到底写过些什么,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因为除了他的自传体的“人生三步曲”外,书店也没有见还有高尔基写的什么书。历史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破坏知识的历史。例如秦始皇,只是因为他焚过书坑过儒,和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基本一样,于是就成了一个有进步意义的好皇帝。至于秦始皇是以暴政而出名的,那不但不是什么罪恶,反而是应该赞扬的进步行为,因为毛主席都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至于承载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那更是空白,因为孔孟之道早在文革初期就都被打倒了。孔子、孟子、老子,这只是一些名字,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曾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思想。尤其是孔子,那时甚至不能称为孔子,因为我们被告知“子”是对一个人的尊称,而孔子是反动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因此是不配称作“子”的,因此我们必须直呼其名叫他孔丘(在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中,对一个长者直呼其名是极为不尊重的),甚至直呼其名都太过优待他了,要叫他的外号“孔老二”,这已几近是骂人了。1968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了,但是我们没有物理课和化学课,更没有生物课和地理课。所以,我的中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这些理科的知识基本上都是零,历史和地理这些文科的知识都是靠自己因兴趣而看了一些书而有了一些零碎的了解,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可以说,我的小学最后两年和整个中学阶段基本上没有系统性地学过任何知识,说是学习知识的空白阶段毫不为过。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6 - 别样人生, 2017-04-19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是爱骄傲,这评价有点熟悉:)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是爱骄傲,这评价有点熟悉:)